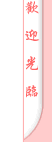|
难以形容,这个故事从开始起的存在状态。我至今不能明白为何自己会义无返顾地选择退出——事实上,我并没有选择过,只是循规蹈矩地一步步走向今天。
这是一种难以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的存在。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你无法改变并且只能接受。
于是,我也就同样不能隐瞒另一个事实的存在:
我们分手了。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痛苦的解脱:在获得自由的同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无助。而我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分手”不同于“甩”或者“抛弃”,它不存在主动者或被动者,也不存在着施动者或受动者,一切均由双方共同做出抉择,所以,更明智,也更冷静,当然也就更没有理由后悔。
在与他一起的日子里,我们之间鲜有步调一致的时候。通常的状况是一个孩子和一个家长,也就是说,一个命令,一个执行。更糟的情况也有——那便是无家长状态:谁都别扭着,不肯让步。然而,在分手这个问题上,我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这不得不叫人感觉有点——
凄凉。
这个故事到现在依然是不正常。不正常的概念也可以用“非常”来表示。套一个时髦一点的词来讲,我跟稷平就是一对“非常男女”:没恋爱的时候,我们像一对恋人,而真正恋爱的时候,我们却又像是一对仇人。
——我的口气听来似乎有点无奈,可实际上,我在讲这些的时候,只是想到了一个很温暖的词汇——
怀念。
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和他之间的岁月是值得怀念的。尽管有无尽的争吵、赌气和冷战,但一切都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也正因为这种拥有,我们才曾经成为彼此的另一部分。无论当时吵得如何激烈、如何不可开交,现在回想的时候,所剩的只是幸福。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只不过是聚在一起吵吵架而已。
可惜,当时并不能明白。
如果一定要用道德标准来评判,那么,变心的人不是我——其实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什么都在变,我又如何知道自己不比他先变心。我这样说并不想表白自己如何大度,说得稍微公正一点,我只不过是没有比他先找到异性朋友而已。所以,以我现在的处境来说,是有那么一点点——寂寥。
我相信我仍然是爱着稷平的,否则我不会退出。至少,不会这样轻易地退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一丝一毫都没有过。我相信我的愿望从来都是要他快乐、要他幸福。所以,当稷平将王逾带到我面前时,我知道,在稷平的生命舞台上,我已经失去了光泽。
王逾并不是那种绝色美女。但从第一眼起,我就心甘情愿地认输了。她平静得有如一面没有水纹的碧色湖泊——说句实话,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到的是“碧色玻璃”。真的,她就像玻璃一样通透、晶莹。而我最终没有用“碧色玻璃”来形容,只是因为:玻璃的世界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虚伪世界,可王逾却绝不会让人联想到虚伪。她的安静带着一种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所到之处,无不为之倾倒。我坚信:稷平不是被她俘获的第一个男人,我也不是被她击败的最后一个女人。她的出现让我猝不及防。不,我甚至都未曾想过要设防。或者说,我也根本没有这个机会——这对我而言,似乎有点不公平,但事实上,女人之间的战争通常很容易决定胜负。有时,仅仅只是个眼神。——接着,稷平的目光就来了。我知道,他爱上了王逾。
稷平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的目光终于在我的久久凝视下变得无路可逃。我尽量显出自己的不在意来。我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的表演似乎有点过火,回头咀嚼的时候,竟是一嘴的滞涩难忍。——你自然是不会懂的。
稷平从背后圈住我的肩膀,脸埋在我的长发里——我曾试图去剪个短发,仅仅是为了稷平,而如今——
长发依旧,人已不同。
“别玩了。”我嗔怪着,用肩膀推了推。
稷平却不动,或许是因为内疚,或许是因为留恋,他迟迟不肯松手。
僵持了好久好久,我站得有点累了,何况背上还有稷平。再接着,我的脖子里便是一阵微微的酥麻,就像小虫慢慢爬过。我一个激灵,说:“帮我叫车去吧。”
我不敢看稷平,是怕自己也跟着他哭。而在这个故事里,是不该有人流泪的。
“别走。”稷平的语气带着一贯的任性却又显得相当虚弱。他松开了手,木然地站着,还看着我。
我盖上箱盖,屈膝坐在宽大松软的塌塌米上—
“其实,稷平,比起现在,我更想念没跟你恋爱的日子。”我说的是实话。
“可是,桑辛……”稷平沉默了半晌之后,终于无语。
我提起箱子,还挺沉。我抬头望着稷平。
“我去帮你叫车。”稷平紧吸了一下鼻子,抹了一把脸,便迅速地转身去换鞋。换完一只,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一蹦一跳地进来,提起我的箱子,然后蹦一步,拖动箱子拉一段,再蹦一步,再拉一段。我听着他换上另一只鞋,然后又慢慢地走下楼梯。我对着镜子扯了扯上衣,又理了理头发,然后走到玄关处换鞋。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同。
一切就如平常。
我拿起钥匙,砰地关上大门。黑色的沉重大门隔绝了屋内屋外两种光亮,也隔绝了我跟稷平的所有过往。我终于开始意识到这地方已将成为我永久的禁区而不能再踏进半步。
一种东西在我体内不断地碎裂、碎裂,然后又缓缓地在我眼里无声地堆积、堆积……
正恍惚,一束灯光从脸上晃过,伴随的是小车的换档声。我扣上鞋扣,蹬蹬蹬地往楼下跑。稷平正从车里钻出来,他的身形一下子湮没在黑色的夜幕中,然后又慢慢地呈现、呈现……我走近车门,稷平伸出双臂一把拥住了我。在他的怀里我感受到了他不同寻常的战栗,或许颤抖的人是我——但无论怎样,这个怀抱将不再属于我了,连同怀里的温度——我轻轻地格开他,决然地低头,在他看见我流泪以前,成功地借着夜色仓皇逃离。
“到了那儿,我会给你挂电话的。”——我下意识地不想让司机胡乱猜测我无助的境遇。
“好,我等着……你,……走好。”稷平杵在那儿,开始掏烟。
这是我所看见的他的最后一个动作。
小车终于绝尘而去,我一直没有再回头,——事实上,我已经不再有这个机会了——三十分钟的车程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坐姿——因为我是坚强的,我的这种坚强叫我不能动弹。
我没有立即回家,拖着箱子四处闲荡。我一直害怕一个人走夜路,尤其是在这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星星很亮,却越发显出夜的黑,黑色的风牵着我的裙摆,一个劲地要把我往夜里拽。夜是危机四伏,陷阱密布的。我的害怕让我不得不用警惕的眼神注视着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行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可我总觉得有人要谋害我。我的这种偏执简直成了一种病态——然而今天的我,终于明白了另一件事:这世上还有远比黑夜更可怕的东西。
我在僻静处足足哭了一个多小时,却依旧无法平息心中的委屈。一见母亲,眼泪又忍不住浮了上来。母亲见我带了行李回来就知道事情不妙,何况我又大哭一场。我知道母亲一向反对我跟稷平从恋爱起便开始同居(但是,能够标志我跟稷平正式恋爱的,就是同居。)但母亲是爱着稷平的,她相信稷平终究会和我结婚。她信任稷平,也信任自己的眼光,却没有想到,我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跟稷平分了。
母亲一直不给我好脸色,她深信我定是做了教稷平无法容忍的事情。无论我怎样解释,她总是一厢情愿地坚持这一点。在不长的一个星期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忍辱负重”,我开始觉得屈辱。我大可不必这样地艰辛与苦涩,倘若我稍稍坚持一下,该走的人也决不会是我。然而,我的崇高却只能让自己感动。除此以外,大概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伟大的,这让我对当初的动机产生了痛苦的怀疑——何苦来哉?
整夜整夜地失眠,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整夜整夜地梦见自己正在关那扇沉重的黑色大门,不停地关,关了又关,关了还在关,一点都不符合逻辑地莫名其妙地关门,关门。此外,还有汽车的换档声,它在我的脑海里轮番轰炸:左耳换完了档,又跑到右耳去换档;右耳换完了档,又跑到左耳去换档;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
我迅速地憔悴下去,两眼发直,双颊凹陷,脸色泛青,喉咙干涩。化妆品是越用越凶,却怎么也掩饰不了我疲惫不堪的眼神。我什么都不想做,也什么都做不了。整天一个劲儿地发呆,在公司里是这样,在家里是这样,甚至连逛街也是这样。
不断地有朋友来看我,谁都知道原因,却决没有人提到稷平,我也不说。大家好象都在打哑谜,其实谁都知道谜底,却又很有默契地避而不谈。
我真的累。晚上睡不好,白天还要猜谜。我觉得快要叮不住了。母亲却还是不依不饶,坚决不肯原谅我。她似乎看不到我的痛苦,或许只是视而不见。她的态度让我不得不开始了某种程度上的怨恨:该受谴责的应该是稷平,而受苦的人却是我。倘若这世上还有公平可言,那么属于我的公平又到哪里去了?我终于肯相信了:为爱而爱的人是只可能是神,人,永远都是自私和要求回报的。
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不耐烦,常常无明火起,大发雷霆。尽管我尽量克制着与别人发生冲突,尤其是母亲。但这种克制仅仅是“尽量”,更多时候我还是像一根火柴一样一触即发。而我跟母亲之间更是硝烟弥漫、战火不断——除了上班,我们有的是机会在一起——
但无论怎样,我都天真地以为事情终归会过去的——不是嘛,太阳照样从东边升起,地球依旧旋转不停。
然而,我却没有料到,生活远非如此简单。
最糟糕的事情不慌不忙地来,只是要让我措手不及——我终于证实了我怀了孩子。第一个发现者是母亲。她疑惑地看着我日渐迟缓的动作,便抬起手往我的小腹轻轻一按,然后,告诉我两个简简单单的字:“有了”。
我去了家颇有名望的大医院,也找了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得到的却是和母亲一样的答案。其实,我也料到了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否则也不会来这家医院找这样一个老太太。
但我还是很失望。抬起头,发现老太太的眼神正越过劣制的塑料镜架不怀好意地直盯着我瞅。我明白她在想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想来踩我一脚——我本能地打算叫她也失望一回。
我握着化验单,慢慢地展露笑容——一种期盼已久而又最终得尝所愿的笑容。老太太始料未及,愣住了,但毕竟是老奸巨滑,她随即也跟着我一起笑了起来:“头一胎吧?”
我含英咀华、满面春风地犹如一个演技高超的优伶,然而一走出妇产科,两颊的肌肉便和心情一样松垮垮地脱落下来。不必问我该怎么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这孩子是必须打掉的。他来的太不是时候——尽管我曾经是多么地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我和他的孩子,甚至在一开始我还有过片刻的惊喜,但这毕竟太残酷,无论对我还是对孩子:我将面临的是一个曾经拥有的回忆;而他将面临的则是一个残破未知的人生,至于他的父亲……
上帝为何存在?就是因为生活总是一错再错。
我自作主张地认为他们是不会怪我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的父亲。因为他的降临并不能给任何人带来福音;相反,苦难、艰忍将如梦魇一般始终围绕,甚至还夹杂着耻辱和羞愧。
既然下定了决心,这种事总是越早办了越好。我在公司里请了一天假,便独自去了医院。周二的医院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负责手术的是个男医生。我本能的有些抗拒,但我毫无办法,除非立马走人。男医生的眼球很凸,这让他的样子看上去很恐怖。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凸出的眼球示意我躺上那张放在屋子中央的手术台。这让我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他凸眼珠的形成原因。
我慢慢地爬上手术台,莫名地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真的害怕,牙齿直打哆嗦。但我还是照着他所示意的,一点都不敢违抗。
我侧过头,护士正托着一盘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手术器械由远及近——他们的眼神跟手术刀一样冷漠冰凉——但我立刻便感受到了另一种彻骨的冰凉,更真切,也更绝望——我清楚地知道,孩子没了。
我平躺着默默回想,整个过程悄无声息,谁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而我就这样与医生暗中勾结,秘密地将孩子杀害。
我换上一条牛仔裤,黑色的Jeanswest。又试着走了两步,还行,倒不了。下一个看上去年纪比我更小,怯生生的,一照见我的面,立刻低下了头。所以照我看来,这种地方最容易遭人鄙视,也最容易获得同情——仅仅是因为感同身受。
我歇在一旁,短短的几步已经叫我气喘吁吁。地面好象存心跟我过不去,我明明看准了踩下去,它却又突然凹进去两寸,没着没落的累出我一身汗。
我的头抵住墙面,双眼紧闭。我开始有点想稷平了,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的嘴唇……所有的一切就像拼图一样慢慢地拼装、慢慢地具体起来。他依旧是那样硕大、魁梧,带着孩子一般的笑贴在我面前,让我艰于呼吸。我睁开眼,却分明看到他正逐渐幻化成一具婴儿的身体在我体内慢慢孕育、成长,吐着舌头的粉红色小脸上还挂着笑,我情不自禁地去抚摸自己的小腹——
可惜,那儿已经空了。
已经空了。
我万般无奈地停住手,先前的那个女孩已经出来了,脸上满是泪痕。
跟我一样。
跌跌撞撞地回家、上楼、掏钥匙、开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浓重的鸡香味——什么都瞒不了母亲。
我木然地立着,兀自犹豫。
“你身体虚,好好补补。”母亲端着一锅鸡汤从厨房里出来。
我看不清母亲的脸,只觉得人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接着就轻飘飘地没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正是晚上,桌上的台灯有点刺眼。我眯着眼四下张望:我的手正握在另一只手中,而这只手正和母亲一起香甜地酣睡。我的肚子有点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刚要抽手,母亲就醒了。
“醒了?喝水吗?”母亲用手指轻轻拂去我额前的碎发。
“不,我,饿了。”
“哦,哦,我去拿。”母亲松开我的手,又替我掖了掖被子。就在她转身离去的一瞬,我看见她抬手拂拭了一下。我空荡荡的脑袋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一样的!”
而我曾经是多么地不屑。
我翻转身,整个人蜷缩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人类的原始时期:一种处于寻求庇护的婴孩状态……
母亲细致地一口一口地喂我喝粥,神情专注而又慈祥,恍若也在时光中倒退了二十多年。
我倒在枕头上,泣不成声。许久以来,压抑在心头的苦楚终于汹涌而出,酣畅无比。
母亲的手抚在我的发上,一遍一遍温柔抚摸。
我逐渐安静下来,嚎啕大哭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呜咽啜泣。
“桑辛,都是妈不好,”母亲又哽咽起来,“否则,你也不至于……”。
“妈,”
“……?”
“我只有你了……”
我又躺了两天,才摇摇晃晃地勉强可以下床。母亲每天给我变着方地给我做好吃的,仿佛是竭尽所能,我一天天地好起来,很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甚至是比以前更好。我有了些力气,开始帮母亲洗洗碗,摘摘菜,还时不时地开开玩笑、聊聊天——一切就如从前:我,还是母亲最骄傲的孩子;她,还是我最爱的母亲……
我心情开朗、神情愉悦地上班下班,同事们怪异地看我,以为我一定有什么奇遇,我不怪他们,因为我也曾获得过他们的谅解。快乐的人是不会被人嫌弃的,我很快又融入了他们的行列。同事们嬉笑着一致认定,必定是有一个神秘人物适时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只不过——
没人相信。
关于稷平,我没有一点他的音讯,仿佛他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所以我跟稷平之间也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尽管很多次我都觉得他就在我眼前,甚至有一回我似乎真的见到他了,但我知道那仅仅是一种幻觉。一种挥之不去的幻觉。这种幻觉让我时常感到窒息、憋闷,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仿佛胸中被硬生生的抽离了一段空气,上不上,下不下,找不到着陆的地方。
我一遍遍地回忆,又一遍遍叨叨地给母亲讲我跟稷平的恋爱故事:在大学里的称兄道弟,毕业后的谈情说爱,同居时的争吵打闹,还有分手时的战栗拥抱……
母亲恬静地听,恬静地想,恬静地看着我,然后又恬静地拉过我的手去,轻轻地拍打两下,无限爱怜,无限同情。
我伏在她的膝上,不再泪流满面,我的烦躁、不安、痛苦、窒息已经在母亲的恬静中安然沉息,无限自责,无限愧疚,我对稷平的沉迷让我失去了对母亲的关怀,而母亲的爱抚又终于让我平息了对稷平的怀恨。
我温柔地望着她,第一次感觉到有和母亲一样的神情在眼底起伏荡漾;第一次感觉有和母亲一样的静谧在心头徘徊流动。
我开始对一些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充满了高昂的兴趣,仿佛被压抑得太久的枝条终于可以尽情舒展。
我心血来潮地想要给母亲做一顿大餐,尽管我的手艺连自己都不敢轻易尝试,但母亲给予了我诸多的期许和鼓励。她相信我可以有精彩的表现,相信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她的这种信任让我有了充分的自信和无畏的勇气。我上蹿下跳、手忙脚乱地终于让一切就绪,我强意克制心底的兴奋,大声呼唤母亲。她正坐在阳台上看报纸,秋日午后温暖的阳光透过淡蓝色的玻璃窗户,没有边际地洒落下来,勾勒出她柔和的面部线条—
宁静、平和。
母亲没有应我,兴许是睡着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她,她的脸晒得通红,透着隐约的笑意。一丝头发挂下来,闪着阳光的色彩,轻触着已经有点稀疏的睫毛,却依旧美得叫人妒忌。
我俯下身,又轻轻地唤她,母亲额头细弱的皱纹丝毫不动,还是没醒。我蹲下身,扶住她的肩膀轻轻地摇她——
母亲的头歪了下来,沉重地倒在我的臂弯里——
生气全无。
“妈——”
世界瞬间崩塌。
母亲走得匆忙,忘了捎上我,还有一桌没有动筷的大餐……
我又一次地戴起了黑臂章,以及一朵黄色的小花。然而我却还是常常会忘记母亲的离去。筷子还是烫两双,碗还是拿两个,总是要到盛饭时,才会抬眼瞥见母亲的遗像——她还是那样美,带着温柔,永远地封存在黑色的镜框中,壁立在客厅的墙上——照片是母亲自己选的,就放在影集的第一页,连同底片。此外,还有一张纸条,叫我一切从简,只是要记得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放在一起。底下压着的是一张全家福,二十三年前父亲转业回来后照的,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三个人头靠头幸福的样子——
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地无处依靠……
即便是看着她,我还是觉得母亲不会就这样离开。我常常会听到钥匙开启门锁的声音,悉悉索索,断断续续。这让我有一种错觉:母亲没走,她还会回来。
可是,她一直都没有再回来过。
屋子变得空荡荡的,连同我的心一样没有生气,我又开始常常发愣,日子也一天天过得糊里糊涂,越来越搞不清楚几号是几号,星期几。除此以外,我还养成了另一项嗜好—不断地重复做着母亲曾经给我做过的那几道菜。
我习惯性地开始发呆,不想出门,也不爱跟人讲话,我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独自徘徊在自己的世界,苦苦思念我所爱过的人。
最让人失望的是,王逾和稷平也终究没有走到一起。稷平终于明白王逾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永远都是他们之间无形的尴尬。稷平试图要重回我身边,但我却走向了穷途末路。就在谁都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的时候。
而我也终于明白我曾经所做过的一切均是一厢情愿地白白操劳。更何况,还牺牲了一个孩子。
我慢慢地揩干净那把灰亮的美工刀,在手腕上比了比,冷飕飕的,没有任何光泽。无论是我的皮肤,还是那把看上去挺不错的美工刀。一切都是灰暗的,连同我可预见的未来的人生。
我竖起刀背,强烈地感受到了刀刃的锋利,还有些痒。我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该结束了。
血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四溅而起,奔流而出。它不急不缓地四处酝酿,然后朝着一个方向激烈涌动,汇成一道,沿着刀子经过的地方蜿蜒蛇行。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官刺激:白皙的肌肤衬着鲜红的血——摄人心魂的美。
不骗你。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我耐心地等着安眠药在我体内发作。
爱在我心里缓缓流过,却像带着温度的血泪一样
无法停留。
绝望的人是没有资格活下去的。
这是我在人间想到的最后一句话……
【后记】
终于写完了。原先是有很多话想说的,但现在,似乎什么都不想说了。
“桑辛”的名字是无意中起的,却不想正是吴语中的“伤心”。这个故事是有点让人伤心。我本不想这样的,只是,难以控制。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和选择的余地。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一回,而且,永不会再有重来的机会。
小时侯,常常听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长大了才知道,其实,生命的标点从来就没有让你自己点划过。也正因为如此,生命才变得残酷。
没打算让“桑辛”走上绝路的,但是,情势急转直下,连我都不能控制。需要说明的是:采取自杀这个极端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她不想活下去,而是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当人类失去了亲情与爱情之后,又有几个能够顽强地活下去呢?
但愿“桑辛”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伤心…… |